《禁书大卖,六个权贵逼我照书演》是难得一见的高质量好文,大根江悦是作者“暴走的恰巴塔”笔下的关键人物,精彩桥段值得一看:【古代同人文写手 男全洁 万人迷 雄竞修罗场】江悦,胎穿进书,就干了两件事:第一,用话本把京城权贵写了个遍,笔名“大根公子”;第二,当朝摄政王拿着同人文堵上门:“敢造谣本王穿粉色裤子?限你七日,找出那混账是谁!”她高价悬赏五百两找出了一群替罪羊:“我怀疑大根公子不是一个人,而是犯罪团伙。”反正人人都是,她没有!直到,马甲蹦跶掉了——冷面王爷把她押在书房:“你喜欢粉色,我穿。”纯情皇子红着眼说:“如你所写,其实我挺喜欢挖墙角的。”死对头将军捏着她下巴冷笑:“抓到你了,是照着书演一遍,还是进大牢?”连禁欲国师都加入战场:“我来领书里的小娇妻。”……她深陷修罗场时,那位“已死”的三皇子突然归来:“做我的妻,或毁了你全家。”江悦当众撕碎婚书,笑看一众权贵:“诸位,我的新书《六路追妻:大根公子今天选谁》正在预售——”“想要结局?”“先追上我再说。”...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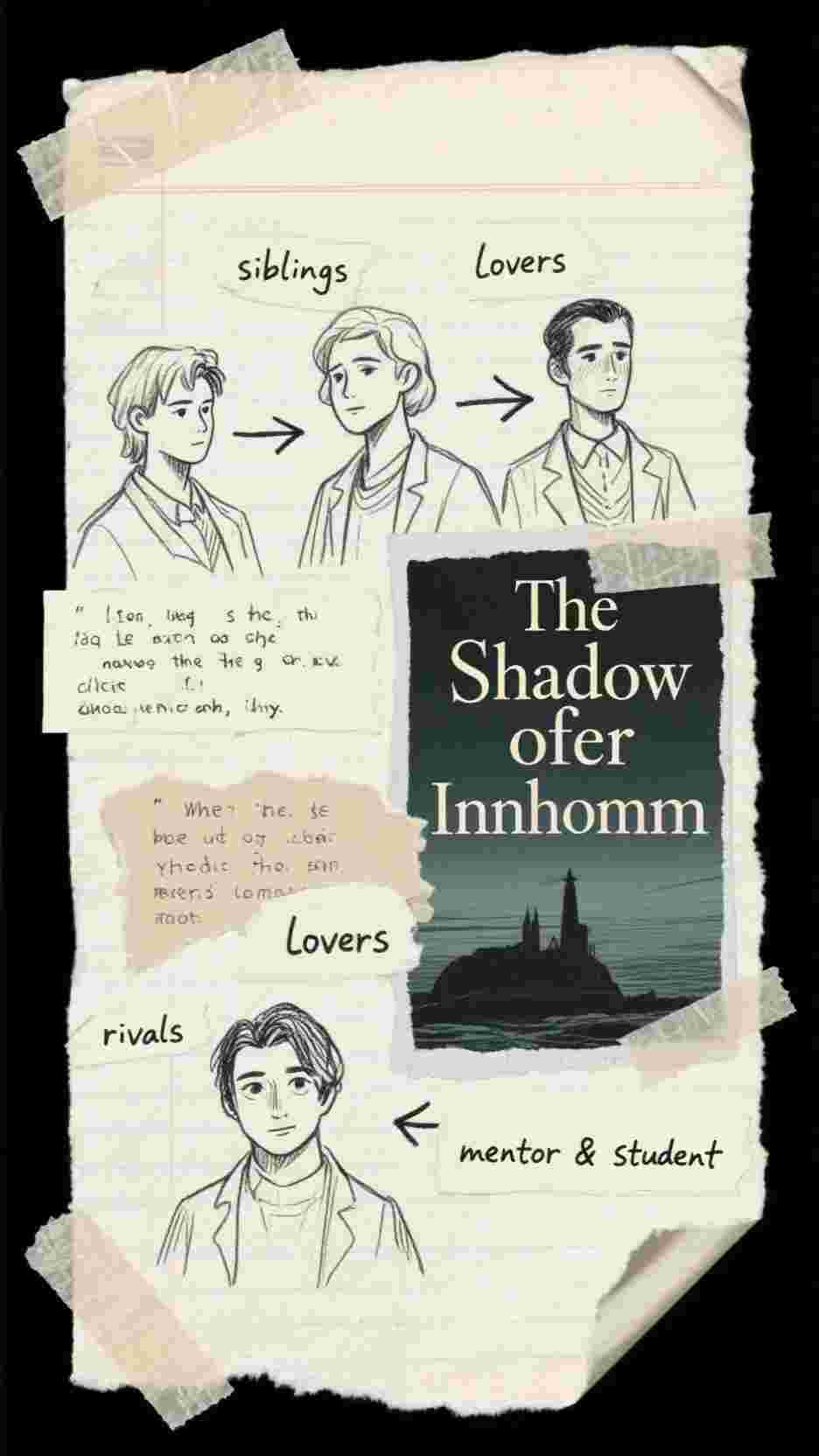
在线试读
萧近宸几乎是靠着本能反应,手忙脚乱地将那本禁书“啪”地一下合上,闪电般塞进了手边的抽屉里,还发出“哐当”一声。
做完这一切,他才板起脸,从旁边抽出一本正经的《北境兵防策论》,重重地拍在桌上。
“站好!”他的声音比平日里更冷硬了几分,“书房重地,不要随意凑近!”
这声呵斥严厉得有些过头,连旁边专心整理文书的江澈都忍不住抬起了头,不解地看向这边。
他冲着江悦使了个眼色,嘴型无声地动了动:别惹他。
江悦撇了撇嘴,不情不愿地站直了身子。
兄妹俩这点小动作,全落在了萧近宸的余光里。他心里莫名升起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别扭感。
想来她又是对自己不满了。
为了驱散脑子里那些乱七八糟的画面,他决定给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“江公子”找点麻烦。
他指着手上的《北境兵防策论》,冷不丁地提问:“你对北境布防有何见解?”
这问题又大又空,寻常书生答起来都费劲,更别说一个闺阁……呃,一个看似文弱的公子了。
问出口的瞬间,萧近宸就后悔了。心里暗骂自己简直是被黄书冲昏了脑子。
谁知江悦只是略一思索,便侃侃而谈。
她从地缘形势讲到各部族的风俗矛盾,再结合原著里透露的一些朝堂秘辛,提出了几个颇具新意的观点。
一套说辞下来,有理有据,逻辑分明,甚至比朝中某些只知空谈的老臣还有见地。
萧近宸听得怔住了。
他端详着面前的“少年”,对方谈论军国大事时,那双眼睛清亮而专注,丝毫没有寻常书生的迂腐气。
“这些见解,不像是寻常闺阁女子,甚至不像一个普通书生能有的。”他几乎是脱口而出。
江悦心头一紧,面上却不露声色,恰到好处地露出一个混合着仰慕与谦逊的笑容。
“家父与兄长常在书房议论朝政,学生听得多了,便记下了一些。何况,学生自幼便将王爷这般守土卫国的英雄视为楷模,对边疆之事,自然也就多留心了几分。”
这记马屁拍得不轻不重,既解释了她见识的来源,又不动声色地捧了晋王一把。
萧近宸果然受用。
他神色稍缓,端起手边的茶盏,想喝口茶压一压心里的波澜。
可当杯沿送到嘴边时,他动作一顿。
只见那青瓷杯沿上,印着一个极淡、却又能辨认出的唇印,边缘还带着一点水光。
他这才想起,这杯子……她刚刚喝过。
自己居然要喝她喝过的水?
换做平时,他早就把杯子扔了。可今天,鬼使神差地,他只是指尖顿了顿,并没有立刻发作,更没有擦拭嘴唇的打算。
江悦看他半天没动静,坏心眼又冒了出来。
她悄悄凑近一步,压低了声音,用只有两人能听见的音量问:
“王爷,水甜吗?”
萧近宸心里一虚,下意识地先瞥了江澈一眼,见他并未注意这边,这才松了口气。
他若无其事地将茶盏送到唇边,轻轻抿了一口。
沿着她的唇印。
然后从容地放下,好似全无察觉两人的间接亲密。
“本王府中的水,自然是甜的。”
声音依旧清冷,只是那微微泛红的耳根,出卖了他此刻并不平静的内心。
就在这时。
书房的门被推开,萧闻那颗毛茸茸的脑袋探了进来。
“皇叔!渴死我了,讨口水喝!”
他嚷嚷着,自来熟地走到一旁的水瓮边,拿起水囊咕嘟咕嘟灌了个满。
灌满之后,他看也没看,习惯性地就把水囊递给了离他最近的江悦。
“江兄,你先喝。”
江悦还没来得及伸手,就感到一道颇具压力的视线落在了自己身上。
她转头,对上萧近宸那张面无表情的脸,故意大声回了一句:“我喝过了,殿下您喝吧。”
萧近宸的视线立刻避开,仿佛被烫到了一般,不敢再看她。
可他的余光,却不由自主地瞟向那边。
只见萧闻毫不在意地笑了笑,仰头就着江悦刚刚拒绝过的水囊口,大口喝了起来。
那熟稔自然的姿态,刺得萧近宸心里极不舒坦。
“萧闻!”他冷冷开口。
“啊?皇叔?”萧闻被吓了一跳,嘴里的水差点喷出来。
“君子之交,当守礼数。”萧近宸的声音里透着一股训诫的意味,“勾肩搭背,同用水器,成何体统?”
萧闻被训得一头雾水,完全不明白自己哪里做错了。
他和江兄不都是男人吗?在军营里一个碗里吃饭都常有,这怎么就不成体统了?
但他不敢反驳皇叔,只能委委屈屈地“哦”了一声,默默地离江悦远了一步,像只被主人训斥了的大狗。
接下来的一个时辰,江悦感觉自己如坐针毡。
晋王殿下不知哪根筋搭错了,一会儿考她兵法,一会儿问她策论,问题一个比一个刁钻。
好不容易熬到江澈与萧近宸有正事要商议,她才得以解脱。
萧闻立刻自告奋勇:“皇叔,我送江公子回府!”
得了允准,两人逃也似的离开了晋王府。
回丞相府的路上,萧闻骑着马,跟在江悦的马车旁,一张脸闷闷不乐。
“江兄,”他忽然开口,“我怎么觉得,皇叔今天对你,有点特别不一样?”
马车里的江悦挑了挑眉:“哪里不一样?”
“他说不出来,”萧闻苦恼地抓了抓头发,
“他从来不会那么有耐心地教人练武,更别提留谁在他书房待那么久了。而且,我总觉得,他今天好像很不高兴我靠近你。”
江悦心里跟明镜似的,嘴上却打着哈哈:“殿下您想多了。王爷那是看我资质太差,烂泥扶不上墙,怕我把您给带坏了。”
“是吗?”萧闻还是觉得不对劲,但他又想不出个所以然来。
他沉默了一会儿,忽然用一种很迷茫的语气,低声说了一句:
“江兄,我有时候在想,你要是个女子就好了……”
这话一出,江悦的心脏猛地一跳,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攥了一下。
她掀开车帘,正对上萧闻那双清澈又困惑的眼。
萧闻被她看得有些不好意思,脸颊微红,却还是接着说了下去:
“我很喜欢跟你待在一起,跟你聊天,跟你一块儿练武。你要是个女子,我就去求父皇给我们赐婚,那我们就能天天在一块儿了。可偏偏你是个男的……”
他说到这里,忽然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,猛地闭上了嘴,脸瞬间红到了脖子根。
完了完了,他怎么能对一个男人说这种话!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