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山河破碎:我与太子共扶倾厦》这部小说的主角是何羡愉雍王,《山河破碎:我与太子共扶倾厦》故事整的经典荡气回肠,属于古代言情下面是章节试读。主要讲的是:在雍王篡位、大燕王朝摇摇欲坠的背景下,靖北侯府唯一幸存的女儿与神秘军傩卫统领的故事。她在淮廊之战中侥幸生还,隐姓埋名调查家族冤案,却在京郊意外救下携血书入京的学子,得知青州灾情被人掩盖的真相。在传递血书的过程中,她与戴着鬼面的他相遇,两人从敌对到携手,共同揭开朝堂阴谋。面对家仇国恨,他们试图扶住这个濒临崩塌的王朝,在凶险的复仇之路上相互扶持,共同面对重重危机。...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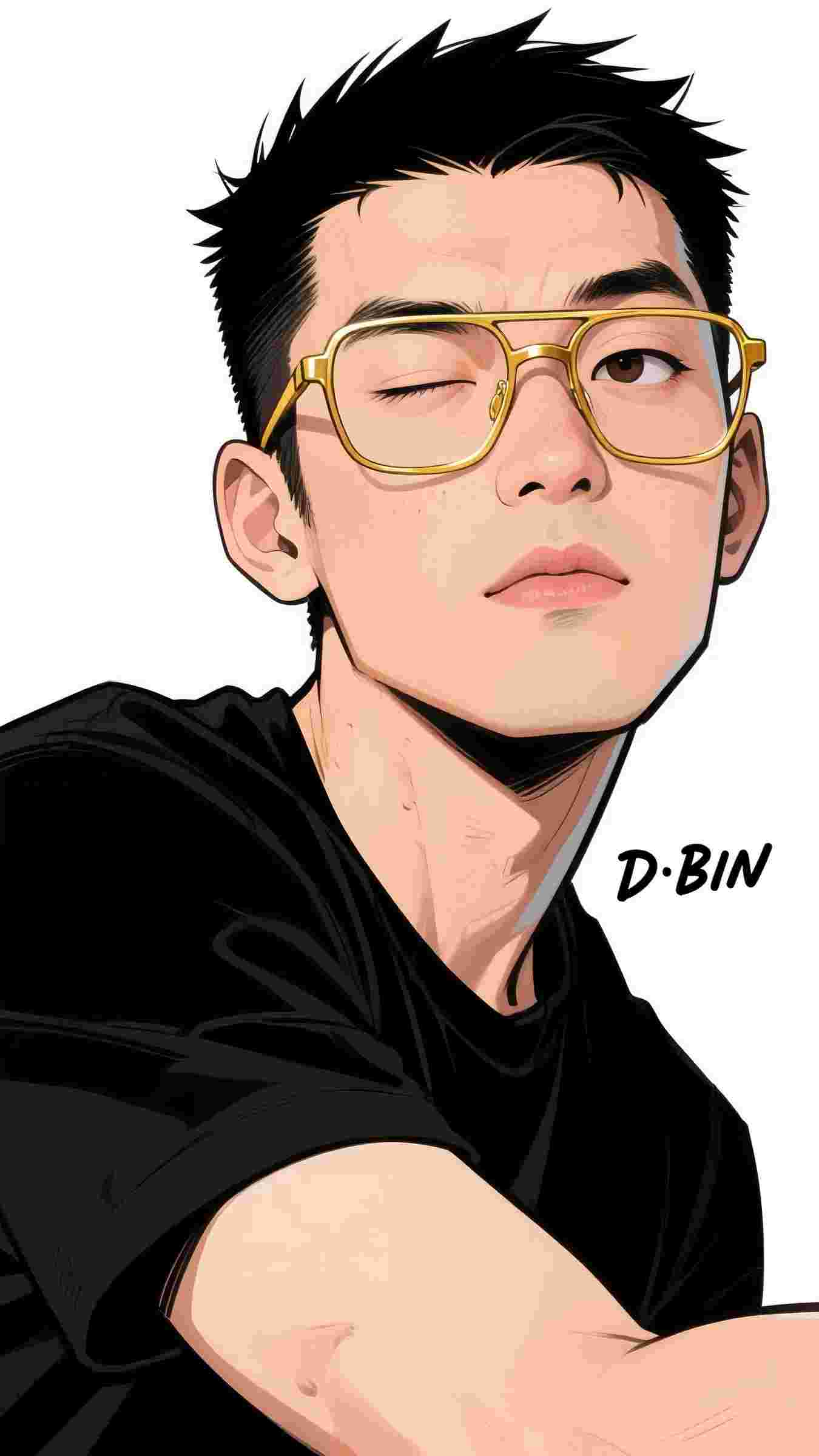
山河破碎:我与太子共扶倾厦 免费试读
青枝抽噎着,把那夜的事一桩桩倒出来。
“那老卒抱着血书把门砸得震天响。我吓得腿软,捧着血书一路奔去找姑爷。姑爷一看,脸当场就白了,连伞都没撑,攥着金符,连夜点兵出城。金符一亮,护城营的校尉一句话都不敢多问。”
“好在大捷。可……小姐回来后就浑浑噩噩,谁唤也不应声,跟丢了魂似的。大家都快急疯了,这半月里都轮着日子守着,姑爷白日处理事务,夜里就坐在您榻边,半步未挪。我半夜进来添灯油,瞧见他攥着您的手,头埋在您腕边,哭得像个孩子……”
门“吱呀”一声被风撞开。
裴忌披着一身寒气进来,玄衣上沾着未干的雨迹。脸色冷得吓人,薄唇抿成一条线,眼尾泛红。
青枝抹了把泪,识趣地退了出去。
他站在榻前,居高临下,浑身绷得紧,这几日都是如此。
何羡愉张了张口:“裴……唔”
后面的话被生生截断。
裴忌俯身,一手扣住她后颈,另一只手撑在她枕边。吻来得又凶又急,牙齿磕到唇瓣,血腥味在舌尖炸开,他不管不顾,舌尖探进去,搅得她喘不过气。何羡愉攥紧他胸前的衣襟,布料在手里皱成一团。
咸涩的液体滑进两人唇齿间,是他的泪。
分开时,裴忌仍维持着俯身的姿势,额头抵着她,泪珠一滴滴砸在她手背上,烫得惊心。
他一句话不说,只是死死盯着她。
“于卿……夫君……”何羡愉抬手,指尖碰到他潮湿的眼尾,“你说句话呀。”
裴忌眼泪一颗一颗往下砸。
“你跟我说说话……”她声音发颤,扯了扯他的袖子,“我醒过来了,你别哭……”
“江愉。”他终于开口,声音哑得像砂纸磨过,带着后怕的颤抖,“你知不知道……”
他顿住,再也绷不住了,猛地把她按进怀里,力道大得几乎勒断她肋骨。隔着薄薄的寝衣,她能感觉到他胸口剧烈起伏,心跳乱得不像话。
“别再这样了。”他埋在她颈窝,声音闷得发狠,“我快疯了……真的快疯了。”
何羡愉轻轻推开,抬手捧着他的脸吻了吻他的额头,却瞧见额头破了皮,脸颊上还有结痂的细痕。
她指尖轻触他额间,心尖一颤,这得磕多少次才会如此。
裴忌不信鬼神,可在她昏迷的这半月。
三跪九叩,日日祈祷。
他跪在佛像前,双手合十,满心敬畏,神佛不为所动。
他哀告无功。
“于卿,阿姐接回来了吗?”何羡愉埋在他怀里,眼眶有些红。
他手轻轻拍着她的背。“嗯,接回来了。”
何羡愉起身,握紧他的手。“我想再去看一眼。”
裴忌点头。待她整好衣冠,两人才并肩踏出府门。
府外早已水泄不通。扬州百姓自巷口排到河埠,竹篮里卧着沾露的鸡蛋,荷叶里包着尚温的糕点,有人甚至倒提咯咯乱叫的活鸡活鸭。
他们见二人出来,像潮水涌堤,只管把东西往她怀里塞。
最激动的是那些被晒得黝黑的渔民,往年开春渔汛,浮栏横江,水匪勒索“海税”,交不起当即掀船,一年辛苦抵不过匪徒一夜赌资。
何羡愉就是他们的救世主。
如今巨奸伏诛,江面再无狼烟,扬州终于太平。
何羡愉冲百姓摆摆手,颔首算是谢过,转身跟裴忌往寒山寺走。
寒山寺钟声清冷,檀烟缭绕。
裴忌将那张人皮铺平,放入棺木,停在佛前请高僧超度。
梵唱如潮,两人默立廊下,看灯焰吞吐,照在棺木上。
孙嬷嬷说,江鸢死时用最后一丝力气碰了碰池中的鱼。
笑着走的。
法事做完后,火化收灰。何羡愉捧出青瓷骨灰盒,盒身尚温,她紧紧搂在怀里。
寺门外古槐系满红绸,风一过,万条霞绦翻飞。裴忌背对她,踮脚将一条新绸挂上最高枝。
“于卿。”
他闻声回头,指尖仓促打结,急步迎上。
“许了什么愿?”
“没许。”他握住她另一只手,“走吧,镖局那些人请客。”
两人并肩下阶。恰在此时,一个七岁的孩子跨进寺门。
粗布青衫,眉清目秀。他与何羡愉擦肩而过,带着风,肩膀轻碰到了她怀中的骨灰盒。
孩子不觉抬头,只看见古槐高处那条新系的红绸,尾端尚未系牢,被风扬起。他上前取下,借了梯子将绸带重新系在最高处。
绸带上的字迹遒劲挺拔,骨力外拓,写着三句话。
此心三愿。
一祈明月高悬,海晏河清。
二祝阿鱼常安,岁岁相见。
三愿大仇既雪,可安枕息。
方丈捻着佛珠上前扶着梯脚,仰头看着少年,满是慈爱,说:“小心摔着。”
这孩子是他从小看着长大的,乖巧懂事,悟性极强。
他回头,嘴角带着酒窝,问道:“刚刚那对夫妻是来做什么的?”
方丈:“上京来的,超度亡魂。”
他若有所思,却被宋今朝攥着后领提走:“别磨蹭,吃饭去。”
酒楼在望。
周横山跟铁柱似的杵在门前,一身腱子肉把衣衫撑得丰满,嗓门却憨厚:“裴大人,老大,里头请!”
裴忌牵着何羡愉的手,边走边说:“周横山昨日找到我,说要随我们进京,入北镇抚司。”
何羡愉挠挠他掌心,笑着说:“那挺好,在身边放心。”
张伯在堂内笑迎,宴席早已布好了。
鲥鱼凝脂,醉蟹堆尖,不比上京皇宫的御膳厨逊色。
楼上,武行简与韩铁胆正低声斥骂蔡宣和,说那狗官暗通南蛮,卖国求荣,视扬州百姓如草芥。
武行简见三人上来,笑着打招呼。裴忌把椅子一拉,把自己搁在武行简与何羡愉中间。
韩铁胆问周横山:“今朝丫头怎么还没来?”
话音刚落,门就被推开了。“来了。”
宋今朝一袭白衣罗裙,身后跟着那青衫孩童。韩铁胆招招手,道:“阿绥,快来韩叔看看,半年没见,都蹿这么高了。”
孩童刚迈半步,厅堂里被风劈开了一道口子。
裴忌指骨一紧,把何羡愉的指尖捏得发白,何羡愉却浑然不觉,目光黏在那孩子身上,一寸不移。
那飞扬的眉尾,微挑的眼角,跟谢烬昭一个模子刻出来的……
裴忌喉结滚了滚,声音哑在嗓子里:“……像。”
“你们也觉得啊,像得邪门。”武行简先回过神,“不会是你们……”
孩童被盯得耳尖泛红,还是规规矩矩作揖:“晚辈阿绥,给诸位叔伯婶姨问安。”
众人见状,这才敢喘大气,可能就是缘分,长得像的人多了去了。
“缘分啊,不如何姑娘将我们小阿绥认做干儿子?”韩铁胆说笑。
周横山给夹一大块塞进韩铁胆碗里,打趣道:“你这个老铁蛋又开始乱点亲戚谱了。”
笑声一层叠一层,烛火跟着晃。
阿绥被韩铁胆他们簇拥着往外走,说要带他去他们击退水匪的地方。他回头,宋今朝冲他抬抬下巴,说:“去吧。”
人散尽了,屋里只剩酒菜味和炭火噼啪。
宋今朝从怀里掏出刚从那孩子身上取下的狼牙吊坠,说:“五年前沧州雪夜,他缩在镖车轱辘边,攥着这个。我看他可怜,就带他回了扬州 ”
何羡愉接过吊坠指尖发抖。
这是当年江俭带着她夜袭南蛮部落时,从射杀的雪狼嘴里撬的,她还笑他没出息被那畜生反咬了一口。
江俭却龇牙咧嘴笑:“小丫头懂什么?四行山的雪泡过的,辟邪!刚好给小侄子做满月礼。”
裴忌身上指腹摩挲着狼牙上的刻痕,声音低而稳:“他右脚踝,可有月牙胎记?”
宋今朝张了张嘴,半晌才找回声音:“……有。你们难道真的……”
何羡愉与裴忌对视一眼。
两人异口同声:“嗯。”
宋今朝愣住。
何羡愉:“我是他阿娘……的妹妹。”
裴忌:“我是他阿爹……的弟弟。”
宋今朝这才吐了一口气,拍了拍胸脯。“照这样说,何姑娘与裴大人早就相识了?”
何羡愉一本正经说:“刚知道。”
酒旗斜倚,晚潮初涨。
三人踩着木桥,一路往黄海子去。
残阳铺在水中,半江瑟半江红。
礁石上,周横山盘膝垂钓,竿尖一点金线垂进水里,嘴里叼着根不知哪扯的狗尾草。
韩铁胆和谢见绥赤着脚追浪花,木桶被甩得叮咣响,笑声撞碎在潮声里。
“于卿,我觉得我还能吃。”何羡愉踢了踢裴忌的靴尖,眼睛却黏在那孩子身上。
谢见绥裤管卷到膝盖,小腿沾着沙,一蹦一跳。
裴忌“嗯”了一声,弯腰捡干柴。他将火石一擦,火苗“噗”地窜起,暖光扑到他脸上,连眉骨的冷峻都被烤软了。
韩铁胆把串好的海鲈鱼架在火上,油脂滴进火里,“滋啦”一声,香气顺着海风爬进人鼻腔。
周横山在一旁骂骂咧咧地刮鱼鳞:“老子钓的,老子还得杀,合着我一人包圆?”嘴里骂着,手里刀却稳,银亮的鳞片飞起来。
宋今朝把谢见绥拉到礁石后,声音压得低。
他仔细听着,指尖无意识地抠着木桶边缘,目光穿过火光,落在何羡愉身上,她正低头捡贝壳,长发被海风吹得乱飞。
“姨母。”
很轻的一声,混着潮声。
何羡愉手里的贝壳哗啦落了一地。
她抬头,眼眶先红了,张开手:“过来。”
谢见绥几步跑过去,撞进她怀里。
何羡愉抱得紧,声音哽在喉咙里:“是姨母不好,把你弄丢了……”
他把下巴搁在何羡愉肩窝,手一下一下拍她后背,像在哄孩子:“姨母没有不好。”
何羡愉松开他,胡乱揉了把他头发,笑着说:“小大人似的。”
谢见绥回头,撞进裴忌的目光里。
那人坐在火旁,手里转着串鱼的木签,火光在他眼里跳动,眉眼和他有五六分像。
“我该叫叔父,还是姨丈?”他声音清亮,带着稚气。
何羡愉笑出了泪花:“换着叫,看哪个顺口。”她轻轻推他后背,“你叔父是个闷葫芦,他也寻了你很久,你的名字都是他取的,叫见绥。乐只君子,福履绥之。”
受了七年的流离之苦,福禄也该落在他头上了。
谢见绥走到裴忌跟前,火光把两道影子拉得老长。
他正试探着喊了声“叔父”,裴忌低低应着,把烤好的鱼最嫩那块挑给他。
不远处,宋今朝和何羡愉并肩站着。
“捡回来的那年冬天,他才两岁多点。”宋今朝踢着沙,“怕我们不要他,夜里偷偷把兄弟们的脏衣服全洗了,手冻出冻疮也不说。”
“谢谢。”
宋今朝屈起指节,在她肩头轻轻一叩:“也算老天开的一桩玩笑。”
何羡愉侧头看着她,说:“那日看你刀起刀落,想必习武多年,窝在镖局里有些屈才了。”
宋今朝扯了扯嘴角,望向远处一线潮:“天下英雄犹如过江之鲫,人中龙凤尚且挤破头,何况我等鱼目。”
“鱼不跳龙门,怎知浪有多高?”何羡愉也学她,在她肩上回了一记,“人总得搏一搏。”
宋今朝低头掸去袖口沙粒,声音被海风吹得有些散:“他们都说,女子就该在闺阁相夫教子,三从四德。可我打小跟着爹走镖,刀口舔血,镖旗扛在肩上,将来还得接他的家业。”
她抬眼看向城里炊烟,苦笑:“扬州的女娘们,一水儿的软语温香,我这样的,媒婆路过门口都绕三步。”
何羡愉弯腰捡起一枚贝壳,指腹蹭去沙:“男子能举杯邀月,女子便可咏絮因风。他们挑灯看剑,我们也能赌书泼茶。同一片天下,同一轮月亮,谁规定长缨与绣帕只能分男女?”
“世人看轻女子的才能,认为她们不必有才华,也不必擅争辩,只需贤良淑德,言传香火。于是用三纲五常当作枷锁,将女子困在深宅大院,却嘲笑女子愚昧无知,心胸狭窄,只知道捻酸蘸醋,碌碌无为。”
宋今朝愣住,潮声忽然静了一瞬。
